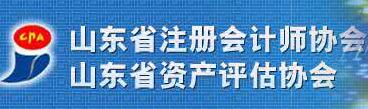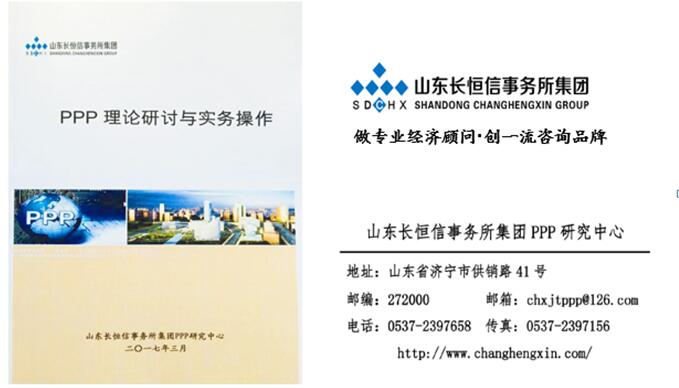在最近幾次重度霧霾期間,環保部調查結果顯示,燃煤排放是華北地區污染的第一大來源。相比于發電用煤,工業用煤以及散煤才是治理霧霾的難題。
來源:騰訊財經
作者:馮軍
今冬,重度霧霾繼續飄蕩在華北上空。12月上旬,北京首次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
治理霧霾,必須先找出“元兇”。在最近幾次重度霧霾期間,環保部組織專家組對霧霾進行實時源解析,結果顯示,燃煤排放是華北地區污染的第一大來源;整個華北地區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億噸,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是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
目前,全國每年消耗大約40億噸煤,約一半用于發電,一半用于工業燃燒和民用。
近些年來,政府大力推行火電脫硫脫硝除塵,2014年7月更是執行了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排放標準,這甚至嚴于一些發達國家。
但目前國際卻又要對發電用煤實行超低排放,這將為此每年多支持上千億的治理霧霾資金。在專家看來,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空間并不大,然而成本卻是巨大的。
同時,這些補貼變相的給一些發電廠帶來了“補貼收益”。
北京國能中電能源副總裁江浩撰文指出,由于脫硫、脫硝、除塵已有補貼2.7分/千瓦時,這一補貼額度刨除成本后每度電還能有0.5分的收益。
補貼收益也促使國有煤電廠已經掀起了一場“超低排放“改造熱潮。
但這股改造熱潮帶來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2015年6月,環保部通報2014年脫硫、脫硝設施存在突出問題的17家企業。
其實,另外一半20億噸的工業燒煤、散煤才是治理霧霾的難題。相比于發電用煤,工業用煤以及散煤的投入以及標準卻遠沒有那么受到重視。
“與火電行業相比,工業用煤、散煤燃燒領域的環保政策落實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緊迫。猶如一個木桶,你不去補短板,而不斷把長板加長,那是沒用的。”專家們指出,超低排放的成本與環境經濟效益不適應,可能花了很大的功夫卻未必很劃算。
千億治霾資金中的漏洞
治霾,成為了2015年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不改“大嘴”的形象,在會上直言三大部委不久前出臺的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方案是“劣幣驅逐良幣”,對治理霧霾作用甚小。
12月2日,國務院召開的常務會議決定,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為鼓勵引導超低排放,12月11日,環保部、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全面實施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分別在2017年、2018年、2020年實現超低排放。即在基準氧含量6%條件下,燃煤電廠力爭實現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濃度分別不高于10、35、50 毫克/立方米。
目前,我國執行的是于2014年7月實施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最高排放標準分別是200mg/m3、200mg/m3、30mg/m3。并對達標排放的燃煤電廠執行環保電價政策。其中,脫硫電價加價標準為每千瓦時1.5分,脫硝電價為1分,除塵電價為0.2分,累計0.027元/千瓦時。據《華夏時報》報道,2014年國家為此需要補貼火電企業約1126.74億元。
按照新政策,上馬“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將在2.7分/千瓦時的基礎上,再加價1分或0.5分/千瓦時。
“只要上了設施,發一度補一度,即便實際上在超標排放都給補,這客觀上就給很多企業鉆空子賺補貼的空間。”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王志軒向《棱鏡》表示。一位環保部官員也對《棱鏡》表示,表面上看達標排放增加了燃煤電廠投入,但實際上是賺錢的,因為里面有“貓膩”。
“脫硫脫硝很多錢是白花了,很多工藝都是白花了。”中國循環經濟協會高級專家曲睿晶透露,國家提出脫硫脫硝除塵達標排放后,很多企業倉促上裝置,有些技術工藝并不成熟,設備壽命短,排放也不達標。
北京國能中電能源副總裁江浩撰文指出,由于脫硫、脫硝、除塵已有補貼2.7分/千瓦時,這一補貼額度刨除成本后每度電還能有0.5分的收益。
一位環保企業的高管也對《棱鏡》透露,除了環保電價補貼外,燃煤電廠還有其他的相應補貼,比如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之類的補貼。目前而言,企業的脫硫脫硝成本逐漸低于2分,節能減排能掙錢,因此電廠也很樂意做。
“電廠做脫硫脫硝除塵治理實際上是賺錢的,有的毛利甚至能達到50%。現在又要加價1分錢,這不是財政浪費嗎?”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對《棱鏡》表示,正是看到有利可圖,電廠都紛紛投入超低排放。
實際上,在超低排放政策出臺之前,國有煤電廠已經掀起了一場“超低排放“的熱潮,都提出了明確的改造規劃。
2015年年初,神華集團國華電力公司宣布,新建電廠全部實現超低排放,同時在2017年前對大部分已投產機組進行超低排放技術改造。大唐集團也不示弱,截至11月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6臺、1551萬千瓦,占全部煤電裝機容量的17.5%;在“十三五”期間還將安排161臺機組進行超低排放改造,預估投資165億元……
超低排放再投入值不值
王志軒是反對超低排放的代表性人物。他對騰訊財經《棱鏡》表示,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空間并不大,然而成本卻是巨大的。
截至2015年10月,我國共有火電裝機量約9.5億千瓦。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每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單價100元—150元的數據測算,如果全面推廣超低排放,將需要上1000億元的改造成本。
從100降到20可能只要10塊錢,可是從20降到10可能要100塊錢。”一位脫硫脫硝設備供應商對《棱鏡》表示,超低排放的邊際成本較大,很難衡量環境經濟效益。
12月27日,在“環境保護’綠坐標’頒獎暨環保創新案例發布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離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基礎,談高標準的環境治理,搞環保大躍進也是不科學的。
目前,我國執行的是于2014年7月實施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最高排放標準分別是200mg/m3、200mg/m3、30mg/m3。
王志軒還計算出,如果燃煤電廠全部達到《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要求,則對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的年排放量分別為367萬噸、182萬噸、55萬噸。如果按照超低排放標準,全國燃煤電廠三項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再削減132萬噸左右,其中煙塵量可下降10萬噸左右。
“132萬噸相對于全國數千萬噸計的大氣污染物來說,所占比重很小。”王志軒指出,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可以判斷出,超低排放對環境質量改善的作用相對較小。
那么已經實行了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運行的怎樣?
近日,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山東、河北、江蘇等地12家宣稱達到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電廠進行了調查,在2015年前三季度的排放數據中,每一家都出現了超過超低排放限值的排放行為。其中某一種或多種大氣污染物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的時間比率超過其總運行時間1%的有5家燃煤電廠,超過20%的有2家燃煤電廠。
“對燃煤機組的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強監管,確保其真實、持續達到超低排放,要防治燃煤電廠以超低排放之名騙取政府補貼的事情發生。”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對《棱鏡》表示。
工業燃煤、散煤才是短板
另外一半20億噸的工業燒煤、散煤才是治理霧霾的難題。
北京市環保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市的燃煤消耗量約1300萬噸,其中常年運行的發電和工業生產消耗是440萬噸,剩下的860萬噸都被用于冬季供暖,且有一半是被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地區的平房居民散煤消耗掉。
“每到冬季,在北方地區的農村,每家每戶的取暖點起來后,未經任何污染物控制的煤煙排向大氣,污染物排放濃度何止發電廠的幾百倍,上千倍,不發生霧霾是不可能的。”中國循環經濟協會高級專家曲睿晶對《棱鏡》表示,河北省一年燒掉的散煤超過3000萬噸,排放未經任何處理,相當于燃煤電廠消耗15億噸煤的排放總量。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王躍思研究員也認為,燃煤電廠的減排技術已經成熟,關鍵是抓投資、抓落實;然而,只抓電力,不抓鋼鐵、發電、建材、化工、民用等其他近50%的非發電用煤是沒用的。
實際上,國家對工業燃煤并非放任自如,也制定了相應的排放標準,只是遠遠低于火電廠的排放標準,而且往往執行不力。“相對于火電來說,冶金、化工、鋼鐵等工業燃煤的排放標準要低很多。”一位脫硫脫硝設備供應商對《棱鏡》說。
一位環保部官員則對《棱鏡》透露,根據環保部對鋼鐵企業進行的全面大排查顯示,70%以上都存在超標排污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鋼鐵企業根本就沒有污染治理設施。
遼寧撫順新鋼鐵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鋼鐵企業,年產量為330萬噸。其副總經理宋亞慶對《棱鏡》表示,近年來國家對鋼鐵行業的環保要求越來越嚴格,公司的環保設備投入已經6億多元,“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出,到發改委申報過,但是沒有獲批。”
相較于工業燃煤和民用散煤領域的“窘迫”,燃煤電廠則獲得了動輒上千億的財政支持。然而這些補貼大多流入了五大國有發電集團的口袋。
公開資料顯示,自2012年初《火電廠大氣污染排放標準》公布后,國內迅速成立了數百家脫硫脫硝公司。作為被改造主體的五大發電集團也相繼成立相關服務公司,如國電龍源環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國大唐集團環境技術有限公司、中電投遠達環保有限公司、中國華電工程(集團)有限公司等。
事實上,五大國有發電集團旗下的燃煤電廠脫硫脫銷除塵的改造工程“內部消化”早已不是業內秘密。
桑德集團總裁文一波在2015年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對《棱鏡》表示,國企在環境治理領域的開放程度并不高,五大發電集團都有自己的脫硫脫硝處理公司,雖然表面上會進行招投標,但是經常暗設門檻,讓屬下的公司中標。
“脫硫脫硝的財政補貼大都被國有發電集團拿掉了,相當于從左手換到右手,而發電集團又內部消化了,這就是一個內部游戲。”邊程認為,財政資金應傾斜于治污相對落后的工業燃煤和散煤領域。
以陶瓷行業為例。該行業的大氣污染物治理措施相對單一,達標企業不足20%:對于除塵治理,主要采用旋風收塵、布袋除塵或水浴除塵;對于脫硝治理,很多企業沒有采用脫硝措施,僅少部分企業進行了簡易的SNCR脫硝;對于脫硫治理,主要以雙堿法進行脫硫,少部分企業采用石灰(石)—石膏法;對于重金屬、氟化物及氯化物等污染物,則沒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
近日,工信部賽迪智庫向工信部提交《加快工業領域散煤清潔氣化技術推廣應用的建議》,指出我國“富煤、少氣”,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尤其是工業領域散煤清潔高效利用是現階段解決我國資源環境制約問題的關鍵。
“與火電行業相比,工業用煤、散煤燃燒領域的環保政策落實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緊迫。猶如一個木桶,你不去補短板,而不斷把長板加長,那是沒用的。”上述環保企業的高管對《棱鏡》說。
國電環保研究院副院長朱法華也指出,“十三五”期間需開拓新的約束性指標減排重點行業;在所有燃煤電廠都可以達標排放的情況下,如果“十三五”期間全國污染物減排仍以電力行業為重點的話,減排效果會很不理想。
警惕火電的“逆擴張”
與我國相反,發達國家正在取消對煤電的政府補貼。
2015年11月17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34個成員國將減少燃煤發電廠的政府投入,逐步合理化取消對化石燃料的補貼。根據協議,美國將限制對出口燃煤發電廠技術的補貼,將使政府對煤炭項目的融資減少85%。
實際上,在加大燃煤電廠補貼的同時,煤價下跌也導致火電成本在下降,這進一步刺激了更多火電項目落地投產。發改委的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火電項目新投產2343萬千瓦,同比增幅高達55%;除了已投產外,各地已獲得路條的火電規模約為2億千瓦。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統計,全球已經有大約1200項燃煤發電廠的建設提案被提出,其中超過四分之三在中國和印度。
“目前已核準和發路條的火電項目的發電能力已超過‘十三五’新增電力需求。”國家能源局規劃司副司長何勇健近日撰文警告,如放任這些火電項目全部在“十三五”建成投產,則2020年火電將達到13億千瓦,比2015年增加3億千瓦,火電過剩會非常嚴重。
科達潔能董事長邊程認為,對火電的過多補貼是“劣幣驅逐良幣”,是對新能源、新節能環保技術的不公平,更不是治理霧霾的好“藥方”。
目前,燃煤發電上網電價為0.3-0.4元/千瓦時,遠低于天然氣發電0.8/千瓦時左右的上網電價。
上述環保企業的高管指出,新能源剛開始發展時產量較少,不具備規模優勢,使得其成本遠遠大于現有的市場價格。在此情況下,政府應該給予適當的財稅支持,使得其能夠存活下來。但事實上,國家卻把大量的財稅支持給予了傳統的火電行業。
給定同樣的當量,燃煤產生的空氣污染為清潔能源的十倍。據環保部的統計,我國常規煤炭占到能源消費的67%,清潔能源占比只有13%,為發達國家占比的1/3到1/4,這是導致霧霾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國的環保措施大部分都是末端治理,比如脫硫脫硝、強化尾氣排放等;但要從根本上解決霧霾的問題,就必須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柴發合對《棱鏡》表示。